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卡拉亚尕奇乡的西部黄金伊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伊犁公司)2022年12月24日发生重大坍塌溃浆事故,造成18人死亡和重大经济损失。2024年6月19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公布《西部黄金伊犁有限责任公司“12·24”重大坍塌溃浆事故调查报告》(下称《事故调查报告》)。报告称,该起事故系伊犁公司以生态恢复治理之名违规回填尾矿料,引发北露天采坑底层断裂坍塌溃浆造成的一起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2024年9月30日,包括涉事伊犁公司6名员工、受委托编制《北露天采坑生态恢复治理方案》(下称《治理方案》)的乌鲁木齐天助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下称天助设计院)2名技术人员在内的8人被伊宁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阿希金矿。受访者供图
该案于2025年6月17日—19日在伊宁县法院进行公开审理,休庭后于7月7日继续开庭,全案庭审一共持续了9天。
对于面临的牢狱之灾,编制《治理方案》的两名参与者,天助设计院法人代表、总经理李金刚、项目负责人甘晓红一直坚称无罪。而旁听人员则表示,通过庭审质证,大量的书证、证人证言证明涉事伊犁公司并未使用天助设计院编制的《治理方案》。辩护人在法庭上称,天助设计院被人嫁祸,李、甘二人遭遇了无妄之灾。
实际上,对该起事故定性的《事故调查报告》,一经发布就引起了争议,导致在应急厅官网上只“存活”了数日被撤下。
上市公司金矿发生重大事故,8人站上被告席
此次庭审,被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涉事伊犁公司6人中,包括伊犁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刘朝辉,一矿矿长、副总经理唐伟等,他们被指控涉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另外两名被告人是天助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李金刚、项目负责人甘晓红,两人被指控涉嫌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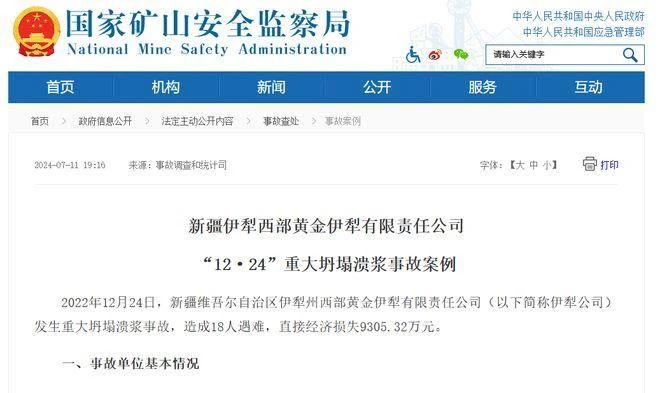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相关网页
公诉方称,2015年,伊犁公司为解决生产中存在的尾矿排放和阿希金矿北露天采坑生态恢复问题,在时任伊犁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刘朝辉的推动下,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阿希金矿北露天采坑综合治理问题,后北露天坑生态恢复治理项目启动。
为推进项目实施,伊犁公司委托天助设计院编制《治理方案》,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以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名义排放尾矿,后来项目申请成功。2016年10月至2022年12月,在向北露天采坑回填尾矿料过程中,时任伊犁公司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的刘朝辉、唐伟、王勇等人长期无视回填尾矿料无法固结的事实,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重大隐患长期存在。2022年12月24日12时20分许,因荷载增大后导致采坑底层断裂坍塌,尾矿浆溃入井下,发生重大坍塌溃浆事故,造成18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9305.32万元。

伊宁县法院。刘虎 摄
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天助设计院编制的《治理方案》存在3方面重大缺陷:(1)设计依据严重失实。一是《治理方案》中“露天采坑底标高1450-1430米留作保安矿柱”,实际已于2004年至2009年采用崩落法完成开采,形成松散废石。二是《治理方案》中“将1385—1400米留作安全隔离层”,实际已于2013年3月至2016年10月,使用下向进路胶结充填采矿法,分别回采了1385-1394米8线—36线隔离层矿石和1385-1400米40线—56线隔离层矿石。三是《治理方案》中“根据矿体倾向1335米中段以下的地下开采活动位于北露天采坑境界外。北露天采坑回填工作不会对地下开采生产影响”的开采现状表述,与实际严重不符。实施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项目后,上部浆体压力逐年增加,隔离矿柱缺失,造成1400米部分巷道发生变形破坏、松散废石层不均匀沉降加剧,对事故的发生有影响。
(2)存在重大技术缺陷。一是没有相应的岩土工程勘察成果,未对采坑边坡情况及地下开采情况进行调查,没有提出有针对性工程措施。二是未进行地基承载力、变形计算,未对底层结构安全性进行分析论证。三是未对底层进行地基承载力、变形计算,未考虑F2断层对地基的影响。
(3)未对工程技术指标进行试验论证。《治理方案》未对推荐的采用灰砂比1:10或1:15,厚度为4米的底层填料工程技术指标是否满足荷载要求、凝结后是否具有防渗水作用进行分析试验论证,未制定底层与边帮结合部位防渗和抗压工程措施。
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因伊犁公司以生态恢复治理之名违规回填尾矿料,引发北露天采坑底层断裂坍塌溃浆,造成的一起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公诉方称,来自伊犁公司的六名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但是天助设计院的李金刚和甘晓红从案发开始就一直坚称无罪,并提起了行政诉讼。

案涉天助设计院(天助公司)。受访者供图
多项“省钱”违规操作,预兆了安全事故一定会发生
李金刚和甘晓红的辩护律师,也对其当事人进行了无罪辩护。
辩护人认为,其是否构成指控犯罪,需要查明最为关键、最为核心且最具前提条件的事实:一是伊犁公司是否按照天助公司甘晓红编制的《治理方案》规划的充填料制备工艺,用于露天坑生态恢复治理项目工程。如果没有采用《治理方案》进行露天坑生态恢复治理项目,则《治理方案》是否属于设计,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治理方案》中有关留作保安矿柱、隔离层当时是否存在等事实,对本案定罪均无实质意义,甘晓红不构成犯罪。
二是如果伊犁公司采用了《治理方案》用于露天坑生态恢复治理项目工程,则需要审理查明甘晓红在编制《治理方案》时是否存在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事实。如果这一事实无法查清,或者说公诉机关不能举证证明,则甘晓红也不构成指控犯罪。否则,就是以法之名冤枉无辜。
在案证据及辩护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伊犁公司完全没有按照天助公司编制的《治理方案》中规划的尾砂充填料制备工艺实施露天坑的生态恢复治理;《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天助公司及其甘晓红等人对“12.24”坍塌溃浆事故负直接责任,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和责任定性错误。甘晓红、李金刚根本不构成指控的犯罪。
公诉机关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的指控,认定甘晓红、李金刚降低技术标准,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但是《治理工程》至今依然是合法有效的(批复的主管部门环保厅、环保局至今也没有撤销该项目的批复文件)、合法合规的,至今也没有哪个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明确不得实施,新发布的生态恢复治理工程标准依然在鼓励该类项目的实施,更为重要的是,从《事故调查报告》到公诉机关,至今没有提出《治理方案》降低了哪个标准的什么指标。这一点,是涉案两位人员及其辩护人无法接受的,“即使我有罪,你也得告诉我错在哪儿了,我也好改正,避免再犯罪吧!”

发生事故的西部黄金伊犁有限公司。图据网络
一、公诉人没有出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伊犁公司实施生态恢复治理项目工程中采用了天助公司《治理方案》规划的尾砂固化工艺进行治理;相反,大量证据证明伊犁公司没有采用《治理方案》规划的工艺进行项目治理,故《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因《治理方案》存在重大设计缺陷导致本案事故发生,证据不足,定性错误。
第一,《治理方案》规划的固化尾砂工艺,概括地说就是尾矿浆通过深锥浓密后,再进行压滤进一步脱水,然后添加水泥搅拌,形成75%浓度的充填料用于露天坑的充填。这不是干排,也不是湿排,而是固化尾砂,使充填料不具有流动性。为此,《治理方案》要求压滤、添加水泥的工艺,在不同的治理环节有不同的表述。
第二,《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与《治理方案》内容不符,有意回避《治理方案》规划的“压滤”这一重要工序。《事故调查报告》将《治理方案》规划的固化尾砂工艺,错误定性为固化湿排,与规划工艺完全不符;《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治理方案》的主要内容中,遗漏了重要的“压滤”工序。
第三,伊犁公司制备露天坑充填料,没有按照《治理方案》工艺进行“压滤”,造成尾砂含水量过大,没有添加水泥或少加水泥或加粉煤灰,无法固结,与《治理方案》工艺不符。足以证明《治理方案》与溃浆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责任。
第四,在庭审过程中,伊犁公司6名被告人都说使用的是天助公司的《治理方案》,但无一人能够详细准确的说出天助公司《治理方案》中北露天坑充填材料制备工艺的要求。尽然还有伊犁公司被告人反问“天助公司《治理方案》要全程添加水泥吗?”,足以说明伊犁公司历任管理者就没有研读过《治理方案》、更不可能有使用《治理方案》的事实。而非法尾矿库与生态恢复治理工程最大的区别就是尾砂是固结还是不固结状态,和改变其物理性质作为充填材料使用还是做尾矿库堆存。
现有证据证明,伊犁公司没有按《治理方案》要求,对尾矿浆进行压滤脱水,致使尾砂浓度与《治理方案》不符,而且证据间存在无法排除、无法解释的矛盾和疑问。其在固化尾砂充填料制备过程中,不添加水泥,或少加水泥,或以粉煤灰代替水泥,采取干排、湿排或干湿混合交替排放尾矿,造成露天坑内排放的尾砂含水量过高,无法固结,形成浆体。伊犁公司在实施北露天坑治理工程施工中无施工资质、无监理严重违规违法,质量无法达标。
伊犁公司也没有按照《治理方案》要求设置排水设施。此事实已经被《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伊犁公司“未按设计要求施工并确保回填尾矿浆固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形同虚设”。没有按照《治理方案》要求,对充填料进行晾晒并分区充填,尾砂无法固结与《治理方案》没有关系。
伊犁公司还违背《治理方案》要求,超采、超量、超时排放,对事故发生造成的影响,与《治理方案》没有关系。
伊犁公司违背《治理方案》要求,在露天坑分区筑坝,堆筑尾矿坝。为了提前使用露天坑,伊犁公司采取分区筑坝,分批排放;采用武汉工程大学的研究报告,在采坑内南端总出入沟口堆筑20米高的尾矿坝,其超采、超限排放尾砂,加之2014年7月至10月,将干渣坝10万吨尾渣倒运到露天坑中,严重增加采坑底部的载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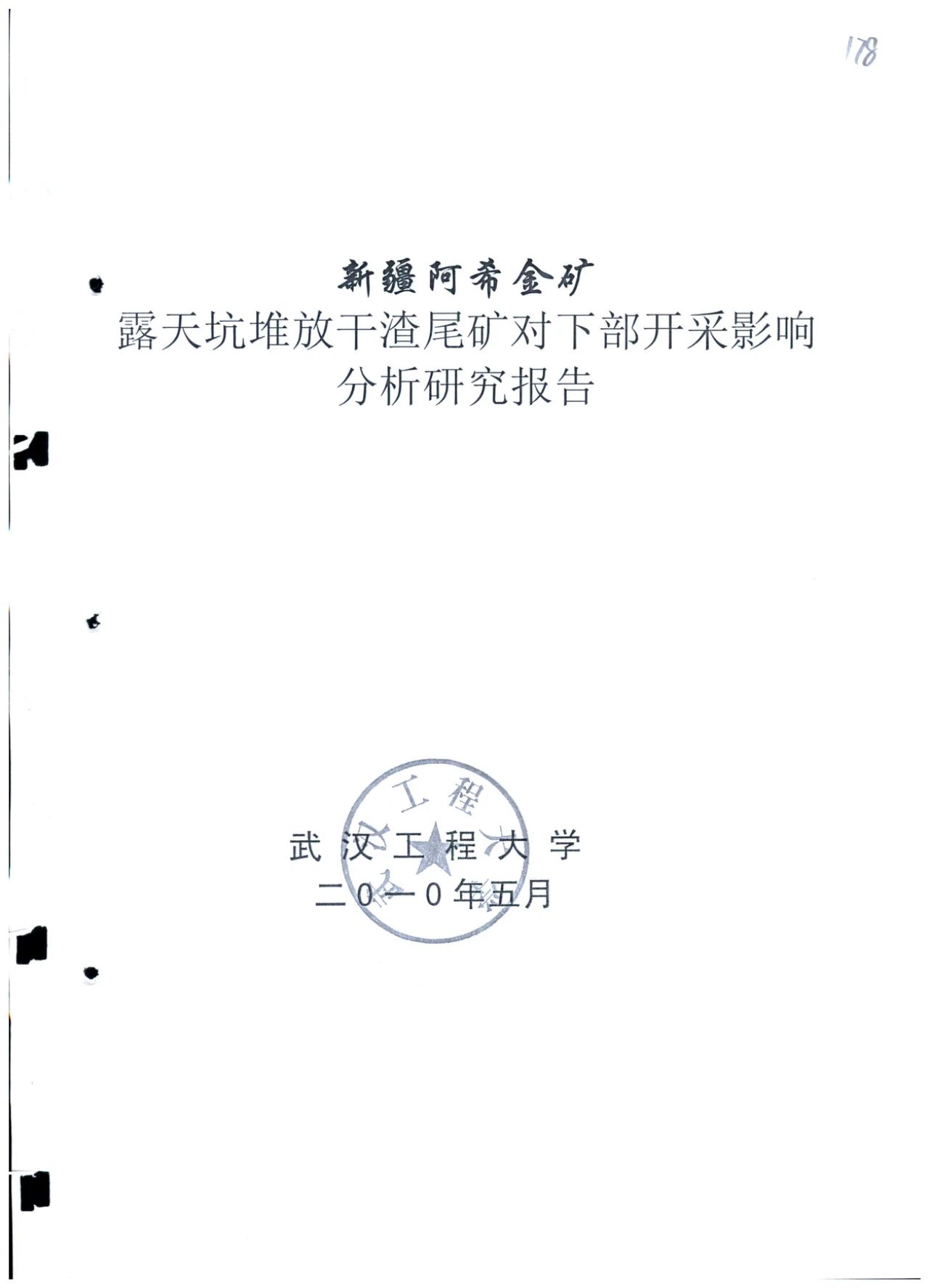
辩护人罗列了《治理方案》中的所有规划的技术要求,一一对比伊犁公司实际的事实情况,表示伊犁公司在实施北露天坑生态恢复治理过程中没有一项与《治理方案》所规划的技术要求相符。
二、《事故调查报告》称《治理方案》存在技术缺陷,对其中有关保安矿柱、隔离层的事实认定,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大量的伊犁公司被行政主管单位批复的采矿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等,均显示保安矿柱和隔离层在天助公司编制《方案》时存在的事实。即使如《事故调查报告》所说,保安矿柱早就被回采,以上证据也充分证明,伊犁公司为掩盖盗采矿柱的犯罪事实,不仅向天助设计院提交了假材料,直至2021年,依然向第三方机构和行政主管单位提交虚假资料。
三、《事故调查报告》错误采信伊犁立洲检测公司出具的《尾砂浆体试验报告》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以尾砂不能固化的试验结论,认定《治理方案》规划的固化尾砂不具有实施性,并将《治理方案》作为造成事故直接原因认定,证据不足。
《立洲公司函》回复称事故调查组并未向其提交天助公司的《治理方案》,该公司并不知道天助公司编制的《治理方案》中制备工艺和参数。试验采用的工艺和参数为事故调查组指定的试验参数,该公司还申明:尾砂样品是由伊犁公司提取的,并且,试验费用是由伊犁公司支付,该公司只提供场所、设备及人员,且立洲公司所编制的《试验报告》并不能提供试验的技术规范和依据,不作为任何案件的证据。
“这不是有意制造伪证吗?”休庭期间,旁听者相互讨论时说到。
四、现有证据证明,伊犁公司隐瞒实际使用长春设计院初步设计(代可研)、飞翼股份公司实验工艺实施尾砂排放的事实,事故发生后推卸责任嫁祸于天助公司编制的《治理方案》。
在法庭调查期间,被告人唐伟在回答甘晓红的辩护人发问时,陈述伊犁公司《治理方案》是用天助公司的,实际是用飞翼公司的尾砂制备工艺对北露天坑进行生态恢复治理。辩护人陈述,这才是本次事故的关键,充填料制备工艺的改变,是溃浆的根源,《治理方案》固化尾砂,没有流动性,而伊犁公司擅自采用长春黄金设计院的充填料制备工艺,浓度过低,实施中又偷工减料,最导致露天坑内大量的尾矿浆无法固结,并最终酿成惨剧。
《治理方案》编制者与辩护人沟通时强调,《治理方案》的核心要点,就是固化尾砂,全文一再强调固化尾砂,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下部还在采矿生产,上部如果是浆料,那是极度危险的,作为一个有十几年矿山工程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来说,这是原则上的原则,不可能违反,更不可能帮助建设单位逃避这个问题。
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大量证据,证明伊犁公司从2009年到2016年通过各种研究、实验、论证和派人现场考察,与飞翼公司十余次技术磋商和充分沟通,经伊犁公司批复,最终确认采取尾矿浓缩+井下采空区充填+露天坑充填的工艺,总投资为2300万元。这足以证明其采用的是长春设计院的初步设计用于露天坑生态恢复治理项目。但伊犁公司向办案机关提供的《北露天坑生态恢复治理项目历史沿革情况说明》中,刻意隐瞒上述整个过程和事实。
五、《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李金刚、甘晓红二人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没有证据证明天助设计院与伊犁公司相互勾结、帮助伊犁公司逃避应急厅监管,将露天坑生态恢复治理项目变相作为尾矿库使用的动机和目的。《事故调查报告》的认定及公安的侦查方向,所谓“天助公司在寻求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同意被拒后,转而绕过监管,向环保部门申请并获得成功,并骗取环保部门的批复”的指证,法庭上除了伊犁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均未参与本项目前期工作,对前期项目的沟通咨询并不知情)的证言外,没有任何有效证据。将与各主管部门沟通咨询的正常业务工作,臆测为帮助伊犁公司犯罪的违法行为,并由此将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强加于李、甘二人,甘李二人的建议量刑均高于伊犁公司被提起公诉的六人。现有证据证明,伊犁公司将北露天坑作为尾矿库使用排放尾矿的想法,早已有之。其因盲目追求降低成本,而利用《治理方案》取得环保部门的同意,目的仅限于通过审批手续,一直谋划挂羊头卖狗肉的事。事故发生后,却嫁祸于天助设计院,致使甘晓红、李金刚及天助公司成为受害者。

提起公诉的伊宁县检察院。刘虎 摄
六、《事故调查报告》对天助公司及其李金刚、甘晓红的责任认定,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丧失客观公正。
参与伊犁公司生态恢复治理研究、论证、设计的单位先后有长春黄金设计院、兰州有色设计院和中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等。相比之下,天助公司编制的《治理方案》是所有方案、设计、研究等成果中,更为优化,最为保守,安全性最优的。只有天助公司编制的《治理方案》是生态恢复治理,其他设计单位的成果中制备工艺均变相的将北露天坑作为非法尾矿库使用。
设计院、案涉员工提起行政诉讼,两审均败诉
2024年10月,天助设计院、甘晓红、李金刚和天助设计院总工程师戴训斌(受到行政处罚)作为共同的原告,就自治区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行政批复一案,向乌鲁木齐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或部分撤销自治区政府作出的《关于新疆伊犁西部黄金伊犁有限责任公司“12·24”重大坍塌溃浆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下称《批复》)。
《起诉状》称,天助设计院并非案涉工程的设计单位,甘晓红、戴训斌、李金刚对案涉工程也不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事故调查报告》和《批复》对事故性质认定及事故原因分析错误,并且调查组成员组成不合法,调查组《事故调查报告》系超期提交。自治区政府在作出《批复》时,未对《事故调查报告》的事故性质、事故原因、处理建议等进行实质性审查,因此,《批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乌鲁木齐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一方面因案涉《治理方案》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事故发生,案涉《事故调查报告》根据事故原因分别对甘晓红、李金刚、戴训斌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符合《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另一方面,自治区政府作出被诉《批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批复》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遂作出了驳回起诉的判决。
一审判决作出后,上述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4月3日,新疆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和一审法院相同的是,二审法院也没有对原告提出的“天助设计院并非案涉工程的设计单位”、“现场未按照天助设计院作出的方案施工”、“伊犁公司采用了马鞍山研究院的技术设计对北露天坑进行回填”等事故原因方面的问题作出审理意见。

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刘虎 摄
虽然目前伊宁县法院还没有对李金刚、甘晓红等人所涉刑事案件作出是否有罪的判决,但是案发后,两人和所在的设计院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个明确被补充委托的咨询文件,并依据环保部门《方案(规划)编制规范》为依据编制的方案,就因文件中带有“设计”二字,被强行认定为设计文件,并要求做各种分析研究,认定未在岩土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基础上编制设计文件,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进而,住建部将天助设计院的冶金专业甲级资质降为乙级。
作为民营企业的天助设计院成立二十年来,本着“自助者天助之,自弃者天弃之”的奋斗理念,在疆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全疆冶金行业甲级资质的本地企业只有二家,天助设计院是其中一家。高峰时,市场占有率一度超过50%,公司成立以来累计为国家纳税几千万元,长期稳定解决50至70名专业和管理、服务类人员的就业,为新疆的冶金行业的快速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受本案影响,公司两年来没有业务,严重亏损,技术人员流失仅剩一二人留守,企业即将解散关门,一支完整的设计团队就此土崩瓦解,两代人的心血付之东流,多位业内人士为之扼腕痛惜。(撰文 | 刘虎)
责任编辑:李霞




